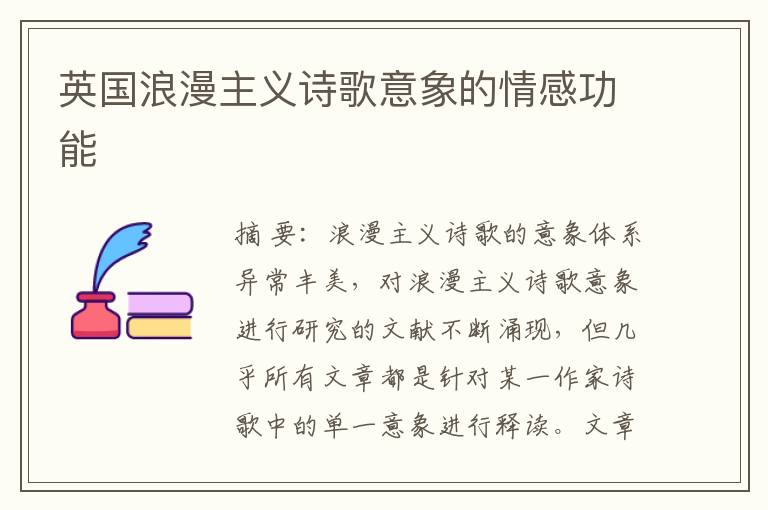我写《百合花》的经过(茹志鹃)
我写《百合花》的时候,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,社会上如此,我家庭里也如此。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,我无法救他,只有每天晚上,待孩子睡后,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,和那时的同志关系。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,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。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,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。有时仅几十分钟,几分钟,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,便一闪而过,然而人与人之间,就在这个一刹那里,便能够肝胆相照,生死与共。
《百合花》便是这样,在匝匝忧虑之中,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。然而产物和我的忧虑并没有直接关系。
《百合花》里的人物、事件,都不是真人真事,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。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,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。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,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,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。那时候,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。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,也正是去借被子。入夜以后,月亮越升越高,也越来越亮,战斗打响了。最初下来的,都是新战士,挂的也是轻花。越到战斗激烈,伤员下来得越少,来的却都是重伤员。有时担架刚抬到,伤员就不行了。担架就摆在院子里,皓月当灯,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,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。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。光从脸上看去,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,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。我要“看见他坐起来,看见他羞涩地笑”,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。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,翻看他们的符号, 记录他们的姓名、单位。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、亲人、朋友,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,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,可能还藏有秘密的、未了的心事……此时此地,此情此景,实在用不着小本本,即便有,也是无从落笔。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,直到现在,清晰度仍然很好,毫不受岁月的干扰。
在那三年风风雨雨,没有白昼没有夜晚的解放战争中,像这样值得追述的事迹太多了。在1958年春寒料峭的夜里,我把它们都翻了个遍。这里再讲两件和《百合花》不无关系的经历。
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! 不知为了什么事,在一个夜晚,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。走之前,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,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,敌人经常向那里打冷炮,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,但不要慌。他不讲倒还好,这一番交代,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。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,他猫腰我猫腰,他走多快我走多快。反正决不在一位战士面前,丢女同志的脸。可是一上了路,他却不愿我傍着他走,要我拉开距离。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,是为了减少伤亡,这也是军人的常识。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,二无树木,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,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、呼啸着飞来,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边靠,在他旁边,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。可是他一见我走近,就加紧步子往前跑,他一跑,我就在后紧追。于是在星光之下,在一片不毛之地上,在怪叫的炮弹声当中,我和他两个人,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,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。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,掉了队,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,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。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,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不记得了。记忆的筛子啊! 把大东西漏了,小东西却剩下了,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。奈何! 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,无声的追逐,却永远是这么色泽鲜明,甚至那野草的摇动,通讯员的喘息,都仿佛还在眼前,响在耳旁。1958年时如此,现在也如此。
另一次情况也是如此:也不知是什么战斗以后,什么战役之前了。记忆中出现的, 已是我和汪岁寒同志来到班里,坐在战士们的地铺上,倾听他们的开会发言(可能是总结吧)。这个班里有一位刚提升的排长,是一位战斗英雄。这位英雄的英勇事迹被时光抹淡了,只记得他很年轻,很怕羞,说说话就脸红。有一次我不知跟他说了一句什么笑话,他红了脸笑着,竟像个苏州小姑娘那样扬起手来,说:“我打你! ”当然没有打下来,但他这种略带女孩儿的姿态,和他英雄的称号联在一起,摄入了我的记忆。晚上,在一间小小的堂屋里,有一张门板搭起的高铺,这原是排长的床,因为优待女同志,就让给了我。英雄则和汪岁寒同志在地上打了个统铺。夜里, 他们头靠头地在轻轻谈话。我居高临下,可以听得很清楚。于是一边装作睡着的样子,一边就竖起了耳朵。抱着极大的好奇心,小心翼翼地想探入英雄的内心世界。可是听听他们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。英雄在谈他的家庭,其中也说到了他还没有结婚,也没有对象之类的内容。他谈得很平常,一点也不神秘。于是我略感失望,就慢慢睡着了。当时虽然有点失望,但后来想想,这倒有好处,起码脑子里印进了一个真实的印象:英雄不也和平常的人一样嘛。
1958年初,那时虽在反右,不过文学上的许多条条框框, 还正在制作和诞生中,可能有一些已经降临人间,不过还没有套到我的头上,还没有成为紧箍咒。所以我在翻箱倒柜一番之后,在过去那些质感的怂恿催逼之下,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,一个年轻的通讯员。我觉得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了,然而我却一直把他搁在一边,冷落了他。他年轻,质朴,羞涩。羞涩的原因是他的年轻。他还只刚刚开始生活,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。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怎么做,我都能推测想象。我当时主要想的就是这些。至于主题是什么,副主题又是什么,主要事件又是什么,我都没有考虑过。
我在确定小通讯员的性格、特点的同时,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“我”,来串起整个故事。在写的过程中,又生出与小通讯员同乡一节,来补充写出他在家乡做老百姓时期的可爱形象,用中秋的一轮明月,来暗写他儿时的生活情景。当时,我就想得这么简单,干得也很利索,很快就写了出来,连抄带写大概用了一个星期。
现在回想起来,可庆幸的一点,是没有按着那一段真实生活来加以描红。而是在原来的生活感受基础上,重新捏出了一个人物,又根据这个人物的需要,再回头来看过去的生活素材,并改造、 综合它们。
我拿来了原生活中与通讯员夜间竞走的一节,但我舍弃了夜间的景色,舍去了炮声的呼啸的紧张气氛;我拿来原生活中通讯员和我拉开距离的情节,但去掉了原因是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,代替以性格。这一段路程的同行,对于刻画通讯员的性格来说,是一段重要的过程。我需要走得从容,紧张的战斗还在后面呢。而且有些内容,即使在一个紧张的军事行动中,也无法表现。 因此,我把它处理在总攻的前夕,一段平静的间隙时间里,使得“我”与通讯员是在完全正常的环境中同行,致使他和“我”拉开距离,更显得突出,也更能显出性格的矛盾,显出他怕女性的那种特定年龄。同时在这段路程中,要让“我”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、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。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。“我”带着类似手足之情,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,来看待他,牵挂他。这个感情建立得越有说服力,那么,小通讯员这一人物在读者心目中也越具感染力。
一点思想准备,想不通的时候。但是倒霉就倒霉吧! 也是活该他晦气,谁让他来走这第一遭,开这第一炮的呢……
从这个思想脉络推下去,到最后她把新婚被子劈手夺来,盖上通讯员的遗体,这一动作就有了内心依据。在这一严重的、肃穆的时刻,才显露出她对这位同志弟的歉疚,表现了她对子弟兵的真认识,真水平,真感情。就在这个时候,也只有在这个时候,作品的意念,人物的命运,合拢了,完成了,能够打上一个句号了。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,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,他也得到了一切。洁白无瑕的爱,晶莹的泪。
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,但不久就退了回来。在那个时候,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,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。当然,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,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。也许想得太复杂了,就没有《百合花》了,说不定。
作品一旦写出,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,主要还是要听评论家的,我自己只是零零碎碎记述一下当时的情况罢了。
(选自《漫谈我的创作经历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)
微信扫码分享